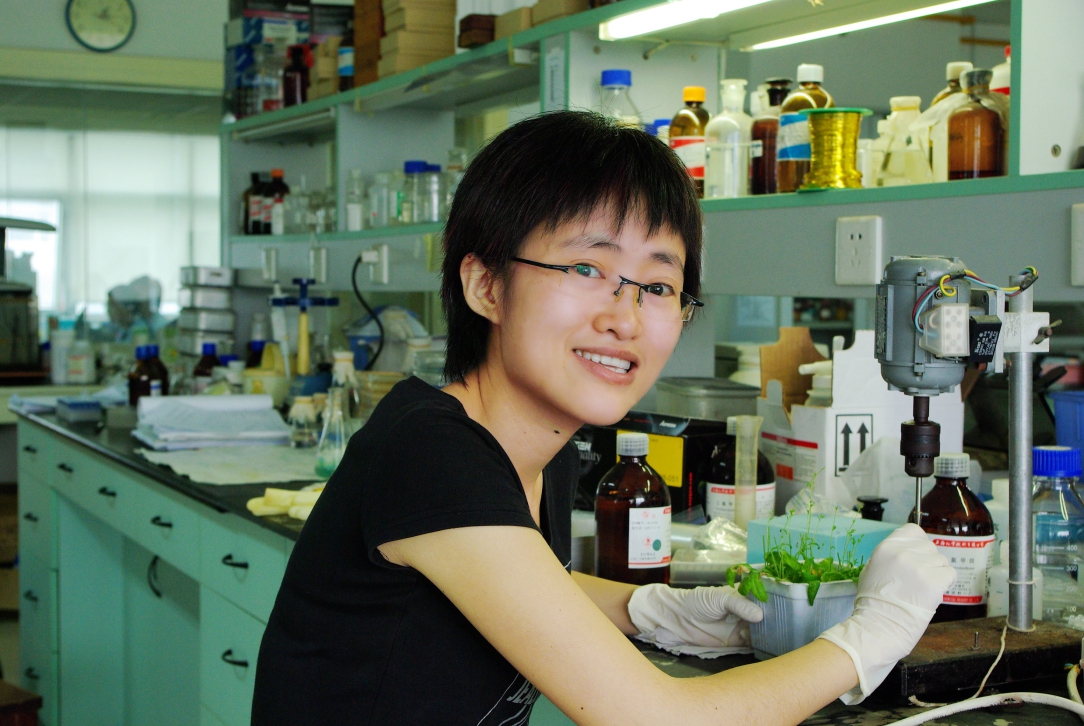寻找小RNA世界里的另一道风景——通往美丽的蜕变
毛颖波
摘要
2007年末,我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的论文作为封面文章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一个看上去平淡的课题,面对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不如意,我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在与同学的交流互助中,令人欣喜的突破出现了。有这样一个童话,一条贪玩的毛毛虫到处游荡不肯象它的同伴们那样吐丝结茧。一天,它看着天上的小鸟,羡慕地说:如果我有一对翅膀该多好呀!蜻蜓说,你不会吐丝,就只能这样爬来爬去。毛毛虫很生气,开始吐丝结茧,最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每一次华丽转身的背后,包含了多少汗水与奋斗。祝愿每一位为梦想奋斗的朋友们,请相信自己就是那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次通往美丽的蜕变。
一九九七年,在举国上下为香港回归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等到了来自江苏某城市的工作聘用通知。我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当时很多同学都忙着考研继续深造,而我因为害怕考研的紧张复习,糊里糊涂的选择了工作。在工作的第一年,我感觉到来自各方面的无形压力,这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一次偶然的人事调动,我被派往北京学习卡介苗(一种预防肺结核的疫苗)生产,我突然觉得自己学的专业其实还挺有用。而我苦恼的根源是因为我不能把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在工作中得到发挥,然而对生物学而言,要想学有所用,仅凭大学本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考研,将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
重返校园
当历史翻开21世纪的新篇章时,我终于成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所的一名研究生。植物生理生态所是由上海植物生理所和上海昆虫所于2000年合并而来,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原昆虫所的蒋容静老师,与原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陈晓亚老师有合作,我因此有幸成了陈老师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入学后的第一年,主要是理论课学习。当时我对分子生物学还非常陌生,有一天下课后,看很多人都围着老师讨论问题,我也非常不解的问道,为什么PCR可以检测外源插入基因呢?结果老师说,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其他同学。现在想来,连PCR的作用都不清楚,简直就是分子生物学的“文盲”。经过一年的理论学习,加上课余时间在实验室给师兄师姐们打下手,我对分子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感情。第一年是开心的一年,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理论知识以及实验手段,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里。等到了第二年,陈老师对我说,你报考的导师从事昆虫科学研究,而我们组研究植物,既然是两个课题组的合作,你应该做选择两个领域交叉的课题。他让我多看些植物与昆虫相互作用与协同进化的文献,对课题的方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一个月后,陈老师再次和我讨论了研究课题。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在植物与昆虫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组长期从事棉花中棉酚生物合成研究。棉酚是有毒的,而棉铃虫却以棉花为食。陈老师建议我研究棉铃虫对棉酚的耐受性机制,寻找棉酚的解毒酶。当时我虽然不知道“棉铃虫对棉酚的耐受性机制”是否可以做好,但毕竟我有了一个明确的课题。
迷雾重重
接下来的一年,我过得很充实,构建棉铃虫的cDNA文库,测序EST,分析棉铃虫中对棉酚处理表达有变化的基因。硕士第三年的时候,我终于找了一个受棉酚诱导的棉铃虫P450单加氧酶基因。也就在那一年,我转成了陈老师的博士生,继续研究棉铃虫P450酶对棉酚的解毒机制。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这个课题很难。昆虫含有大量的的P450单加氧酶,要想确定某种新的P450的底物就像大海捞针。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棉铃虫P450进行酶活分析,但都失败了。看着身边的前辈们,一开始课题也可能是云里雾里,但在最后一、二年都有了可喜的发现,苦尽甘来,我常常想自己的课题什么时候才能有突破呢?四年级了,也开始考虑收获论文的事了,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课题不仅难做,而且比较冷门,相关的论文都发表在一些不起眼的小杂志上。怎么办?换课题恐怕为时已晚,老师也不会同意呀!如果就这样耗到毕业,又觉得对不起自己。当年那么辛苦的考进来,为的是将来能有一番作为,难道就这样黯然毕业,一事无成?真是着急呀,我常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在半夜惊醒,浑身是汗。那一个时期,心情特别郁闷。
渐入佳境
那一时期,国际上对RNA干扰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很多研究小组都有了惊人的发现。我的一个师兄,正好也对小RNA领域感兴趣,他对工作始终充满热情,经常和我讨论科学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带着羡慕的心情听他讲,但我从没想过我的课题也可以赶上“RNA干扰”这个时髦。看到我的工作遇到了瓶颈,陈老师开导我:“虽然研究工作遇到了困难,但是不能知难而退,要尝试新办法”。在与老师和同学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能不能用RNA干扰的方法抑制昆虫的P450基因的表达?如果这个P450表达受到抑制,棉铃虫对棉酚的敏感性会不会改变? 然而,棉铃虫的转基因操作非常困难,怎么才能让棉铃虫体内产生相关的干扰RNA呢?有文献报道通过微注射直接把dsRNA导入感兴趣的组织,可是棉铃虫幼虫个体较小,对注射技巧的要求很高。几次实验下来,发现注射还对幼虫产生伤害,严重干扰后续实验和数据采集。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将dsRNA导入靶组织的文献,发现,Fire等人在98年报道,通过饲喂表达dsRNA的细菌,就能抑制线虫中相应靶基因的表达。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获得了诺奖。我大胆提出,把相关的双链RNA(dsRNA)转入植物中,然后用转基因植物饲喂昆虫,通过取食把dsRNA带入到昆虫体内。陈老师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有创意!”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新的工作。
然而,在接下去的两个月中,我遇到了一些实验上的困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看着毕业的日子渐渐临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渐渐的没有了工作热情。陈老师发觉了我的变化,鼓励我,作科学,要踏踏实实,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被困难吓倒。我很庆幸能遇见这样一位好导师,对学生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科学引导,客观对待,必要时给与鼓励。当时我就像是站在门边上的冒险者,犹豫着该不该跨进屋去看看。陈老师的一番话,给了我朝前走的勇气。在陈老师的指导下,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由于我们的工作直接证明了植物中的dsRNA可以通过取食进入昆虫细胞,行使RNA干扰的功能,为RNA干扰在作物抗虫上得到应用提供了可能性,得到了国际同仁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我也因此体面的毕业了。
毕业以后,我选择了留在研究所继续研究植物与昆虫的互作。如今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家,一份值得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每每看到那些刚刚毕业或走上社会或继续深造正在为明天奋斗的大学生,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未来的彷徨,对现实的无奈加上工作上的失败,使得很多人产生挫败感,其中的一部分人变得像我当年一样的懈怠。对于他们,我想说一句很老套的话: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每一次华丽转身的背后,包含了多少汗水与奋斗。相信自己就是那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次通往美丽的蜕变。至于我,虽然相比同年龄的同学我多花了3年时间给自己定位,但最后我终于转型成功。我希望我是那只破茧而出的蝴蝶,面对这五彩斑斓的世界,能飞得更高更远!